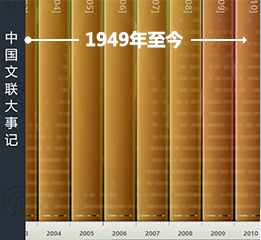□ 趙麗宏(全國(guó)政協(xié)委員)
畢加索是在世界美術(shù)史上創(chuàng)造了很多奇跡的人,他留在世界上的作品成千上萬(wàn)。他一生都在創(chuàng)造新的畫(huà)風(fēng),如此大膽探索,求新求變,可謂前無(wú)古人,后乏來(lái)者。
在圣彼得堡的埃爾米塔什博物館,畢加索的畫(huà)也有數(shù)十幅之多。如果看了中世紀(jì)以來(lái)的歐洲油畫(huà),再看畢加索的作品,確實(shí)會(huì)感到這些畫(huà)是來(lái)自兩個(gè)完全不同的世界,出自兩個(gè)完全不同的時(shí)代。古老的寫(xiě)實(shí)傳統(tǒng),在畢加索的油畫(huà)中碎裂了,顛覆了,荒唐怪誕的形象和畫(huà)面折射出畫(huà)家心里的奇思幻想和動(dòng)蕩不安。畢加索的作品常常使人驚愕,使人不知所措。喜歡畢加索的畫(huà),曾經(jīng)是一種時(shí)髦。面對(duì)他的畫(huà),盡管很多人為之困惑,但誰(shuí)愿意做《皇帝的新衣》那個(gè)說(shuō)“什么也沒(méi)穿”的孩子呢?
誰(shuí)也不會(huì)否認(rèn)畢加索的偉大,不會(huì)否認(rèn)他的生機(jī)勃勃的創(chuàng)造能力。但我相信不會(huì)所有的人都喜歡他的畫(huà)。畢加索那些變形的人像,把美女畫(huà)得面目猙獰、五官不齊,畫(huà)成非人非鬼的怪物,這當(dāng)然是畫(huà)家驚世駭俗的創(chuàng)新,但要說(shuō)這樣的創(chuàng)新令人賞心悅目,那就是假話了。我看過(guò)畢加索為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畫(huà)的一幅畫(huà),那是俄羅斯芭蕾舞演員奧爾加,她身著一襲黑色長(zhǎng)裙,拿著一把扇子坐在沙發(fā)上,眼神中含情脈脈,是一個(gè)絕色美女。那畫(huà)的名字是《坐在沙發(fā)上的奧爾加》。那時(shí),畢加索早已開(kāi)始他的創(chuàng)新,但他畫(huà)的奧爾加完全是自然主義的寫(xiě)實(shí)。畫(huà)布上的奧爾加和生活中的本人一樣美貌動(dòng)人。我想,如果把奧爾加畫(huà)成面目猙獰的怪物,那位美麗的俄羅斯美女一定不會(huì)高興。在埃爾米塔什收藏的畢加索作品中,也有幾幅用傳統(tǒng)手法創(chuàng)作的,譬如畫(huà)于1902年的《索列爾像》和《幽會(huì)》,那是很寫(xiě)實(shí)的畫(huà),表現(xiàn)了高超的寫(xiě)實(shí)能力和傳統(tǒng)繪畫(huà)的扎實(shí)基礎(chǔ)。畫(huà)這兩幅畫(huà)時(shí),畢加索才二十一歲,還沒(méi)有成大名,也沒(méi)有形成自己獨(dú)特的畫(huà)風(fēng)。畫(huà)中的索列爾先生不知何許人,從他的眼睛中流露出的憂郁和期待,使觀者面對(duì)著他陷入沉思,而畫(huà)面上那近乎黑色的背景,營(yíng)造出深邃神秘的氣氛。索列爾先生面前的桌子上放著兩只杯子,一只咖啡杯,一只玻璃茶杯,這兩只杯子值得注意,它們的描繪方式和傳統(tǒng)的繪畫(huà)不同,寥寥數(shù)筆,也不注重形體的精確,卻畫(huà)得很生動(dòng)。這和整幅畫(huà)似乎不協(xié)調(diào),但此畫(huà)卻因此而顯得特別。再看《幽會(huì)》,也是很傳統(tǒng)的筆觸。兩個(gè)身披長(zhǎng)袍的女人,在一個(gè)幽暗的所在相會(huì),兩人觸額相依,似在低聲傾訴別情。有人稱(chēng)這幅畫(huà)為《兩姐妹》,大概是為了避免引起歧義,免得讓人聯(lián)想起同性戀。畫(huà)中的兩個(gè)女人身體的比例很準(zhǔn)確,沒(méi)有什么變形和夸張,但有一個(gè)細(xì)節(jié)引起我的注意:畫(huà)面右側(cè)的那個(gè)人物,放在胸前的右手出奇的小,小得不成比例。這非常奇怪,一幅寫(xiě)實(shí)的畫(huà),出現(xiàn)這樣的比例失準(zhǔn),似乎不合常理,以畢加索的寫(xiě)實(shí)功夫,不應(yīng)該出這樣的差錯(cuò)。這難道是他的故意所為?如果是米開(kāi)朗基羅和達(dá)·芬奇的畫(huà)中出現(xiàn)這樣的比例失調(diào),那必定會(huì)被認(rèn)為是敗筆,而在畢加索筆下,這卻是正常的。因?yàn)椋退髞?lái)的變形相比,這只小手實(shí)在算不了什么。但他的畫(huà)中人物日趨變形卻人人都能看見(jiàn)。在埃爾米塔什所藏的畢加索作品中,有一幅題為《友誼》的畫(huà),畫(huà)面是兩個(gè)依偎在一起的女人,那是變了形的人體,但還能分辨出人的臉,臉上也還有具體的表情。這表情,使我聯(lián)想起《兩姐妹》。我覺(jué)得這是兩幅內(nèi)容和意境相近的畫(huà),但《友誼》和《兩姐妹》在風(fēng)格上已經(jīng)大相徑庭。再看他中年以后的畫(huà),譬如著名的《哭泣的女人》《斜倚的女人在閱讀》《茶女》等,人物的五官已經(jīng)在臉盤(pán)內(nèi)外隨意跳躍,身體的器官則自由不羈地在畫(huà)面上到處飛舞,被肢解的人和鬼魅、怪物之間沒(méi)有了界限。畫(huà)家如此表現(xiàn)女性,實(shí)在有點(diǎn)殘酷。這些躁動(dòng)不安的畫(huà),和沉靜的《兩姐妹》相比較,真有天壤之別了。在畫(huà)家來(lái)說(shuō),這是變革,是超越,是對(duì)藝術(shù)奧秘的探索,對(duì)觀者來(lái)說(shuō),則是窺見(jiàn)了一個(gè)幻想者荒誕不經(jīng)的夢(mèng)境。有這樣一個(gè)故事:在意大利,畢加索曾為俄羅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畫(huà)過(guò)一幅肖像,作曲家離開(kāi)意大利時(shí),邊防軍人查他的行李,扣下了畢加索的畫(huà),因?yàn)樗麄冋J(rèn)為這不是肖像,而是一幅地圖。斯特拉文斯基百般解說(shuō)也沒(méi)有用,最后只得將畫(huà)送回羅馬,后來(lái)通過(guò)外交官的外交信袋將畫(huà)帶給了他。軍人把畢加索的人像畫(huà)看成地圖,當(dāng)然是一個(gè)笑話,但由此可見(jiàn)這樣的畫(huà)和傳統(tǒng)的肖像有多大的差別。
在埃爾米塔什博物館,有一幅畢加索的畫(huà)題為《持扇的女人》,畫(huà)于1908年,畫(huà)面上一個(gè)半裸的女人,手持一把折扇,坐在沙發(fā)上低頭沉思。此畫(huà)的風(fēng)格已不是傳統(tǒng)的寫(xiě)實(shí),人體雖沒(méi)有大變形,但筆觸和古典的油畫(huà)完全不一樣了,女人的身軀、肢干和臉部表情都被抽象成幾何形體,色彩濃烈,引人注目,這也屬于畢加索的立體主義的實(shí)踐。當(dāng)時(shí),已經(jīng)有人稱(chēng)畢加索為“瘋子”,但有意思的是,那些把畢加索稱(chēng)為“瘋子”的人,卻愿意出巨款收購(gòu)他的畫(huà)。看《持扇的女人》時(shí),我很自然地想起了畢加索為奧爾加畫(huà)的肖像,《坐在沙發(fā)上的奧爾加》畫(huà)于1917年,比《持扇的女人》晚了十年。以我所見(jiàn),為奧爾加所作的幾幅畫(huà),是畢加索留存世間的最為寫(xiě)實(shí)的一批畫(huà)。而奧爾加坐到他的畫(huà)室里時(shí),他已在變形的道上走了十多年,他的立體主義正向著巔峰發(fā)展,作品中已很少出現(xiàn)傳統(tǒng)的寫(xiě)實(shí)筆墨。但他卻為奧爾加的肖像選擇了一種古典的風(fēng)格,這件事情很值得玩味。奧爾加是畢加索的妻子,他曾經(jīng)為她畫(huà)過(guò)很多肖像,沒(méi)有一幅是用立體主義的手法完成的。我讀過(guò)畢加索的傳記,傳記中說(shuō)奧爾加不懂藝術(shù),一定要畢加索用古典的繪畫(huà)方式為她畫(huà)像,而畢加索則對(duì)她言聽(tīng)計(jì)從。畢加索是一個(gè)固執(zhí)孤傲的人,不會(huì)輕易就范于別人的指點(diǎn),即便是沉溺在戀愛(ài)中時(shí),他也不會(huì)放棄對(duì)藝術(shù)的執(zhí)著追求。他的一生,是不斷戀愛(ài)的一生,誰(shuí)也無(wú)法統(tǒng)計(jì)曾有多少女人進(jìn)入他的情感生活和性生活。而與此同時(shí),他也在不斷地更新自己的繪畫(huà)面貌。如此耐心地用自然主義的手法畫(huà)肖像,在畢加索實(shí)在是難得。其實(shí),不僅是奧爾加,畢加索在畫(huà)他所愛(ài)戀或敬重的人時(shí),總是避開(kāi)了立體主義,停止了他創(chuàng)新求異的步履。譬如他的母親,他的幾個(gè)好友,在他的筆下都是自然的形態(tài)。那么,在畢加索的心里,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,這也許是一個(gè)秘密。但很顯然,在創(chuàng)作手段上求新求異的結(jié)果,未必是藝術(shù)家理想的美妙境地。我相信,那些面目猙獰、肢體錯(cuò)亂的繪畫(huà),很可能是激情和仇恨交織的產(chǎn)物,而柔情和浪漫的糅合,應(yīng)該產(chǎn)生令人身心愉悅的效果。
“當(dāng)我看著你時(shí),已經(jīng)再也看不到你。”當(dāng)年,畢加索談他的人像畫(huà)時(shí)曾經(jīng)這樣說(shuō)過(guò)。這是一句充滿玄機(jī)、似是而非的話。我想,這句話中,第一個(gè)“你”,是畫(huà)中人,而第二個(gè)“你”,應(yīng)該是被描繪的對(duì)象。如果是這樣,那很符合畢加索作品欣賞邏輯。
1911年,美術(shù)評(píng)論家米多頓·墨利寫(xiě)了一篇關(guān)于畢加索的文章,發(fā)表在倫敦《新時(shí)代》雜志上,文中有這樣的話:“我極為坦率地表示決不假裝理解或是賞識(shí)畢加索。我對(duì)他敬畏有加……我站立一旁,深感懂得太多而不敢妄加責(zé)難;同時(shí)又感到懂得太少而不敢隨意贊美。因?yàn)榧偃绮皇钦f(shuō)空話,贊美是需要理解的。”墨利的這段話,大半個(gè)世紀(jì)以來(lái)一直得到很多人的共鳴,因?yàn)椴皇撬腥硕际菬o(wú)原則地追求時(shí)髦,盲目地追新求異,不是所有人都會(huì)去贊美自己并不理解的東西。記得在八十年代中期,曾經(jīng)有一個(gè)頗具規(guī)模的畢加索畫(huà)展在上海展出,面對(duì)著畢加索那些立體主義的油畫(huà),人們的目光中有驚嘆,也有困惑。而我,腦子里回旋著墨利的那段評(píng)論,我覺(jué)得他說(shuō)出了我的感受。
有人說(shuō),畢加索是命中注定要成功的畫(huà)家,不管他怎樣玩花樣,伴隨著他的總是榮譽(yù)和成功。在瀏覽畢加索生前的成功時(shí),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梵·高。梵·高和畢加索一樣勤奮,一生都在創(chuàng)造,在探索,但他活著的時(shí)候卻和成功沒(méi)有一點(diǎn)緣分,和他做伴的只有孤寂、落寞和失敗。命運(yùn)對(duì)于不同的藝術(shù)家,竟會(huì)是如此不公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