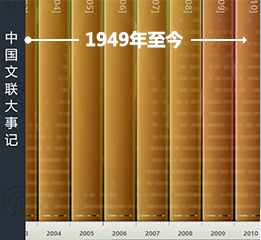捷克僑民斯泰潘,1960年出生,9歲隨父母來到荷蘭,并成長為一名設(shè)計(jì)師。近日,這位游走于不同文化間的“異鄉(xiāng)人”講述了自己的家庭故事、文化體驗(yàn)和文化心理。
和很多捷克人一樣,1969年,斯泰潘的父母帶著兩個(gè)兒子離開了祖國。“沒有任何人知道我們要離開,因此也沒有告別,我們不得不放棄一切。”斯泰潘說。“我再也沒有看到過爺爺奶奶。”斯泰潘至今為之深深悲傷。一家人在荷蘭弗里斯蘭省的朋友家里住了3個(gè)月。“兩周時(shí)間里,我高燒不退。”斯泰潘說,“我叫它‘抑制性發(fā)燒’,抑制失去故鄉(xiāng)的痛苦。”“除了記得當(dāng)時(shí)不斷念叨著要回布拉格找爺爺,我已經(jīng)記不得其他任何事情。”
后來,斯泰潘的父親找到了一份臨床心理醫(yī)生的工作,舉家搬到鹿特丹附近的呼維萊特小鎮(zhèn)。再后來,全家搬到了海牙。
“1990年5月,我飛回布拉格。發(fā)現(xiàn)大家都非常感性,整個(gè)社會朝氣蓬勃,百廢待興。我見到了留在那里的家人,帶他們?nèi)チ耸欣镒詈玫牟蛷d。不管你信不信,我們9個(gè)人的花銷還頂不上在倫敦一個(gè)人吃飯的費(fèi)用。”斯泰潘此時(shí)已經(jīng)是個(gè)青年了,故地重游激發(fā)了他的想象。
“這座城市過去和現(xiàn)在都很美。在一個(gè)小男孩的眼睛里,布拉格是我玩耍、生活過的地方。在一名設(shè)計(jì)師的眼睛里,布拉格的建筑風(fēng)格多樣,可以說是一場視覺的盛宴。我非常感謝父母,正是他們的英勇決定,給了我獨(dú)特的視角。”
此后,斯泰潘每年都要回捷克。他認(rèn)為自己非常幸運(yùn),能夠?yàn)榻菘酥O(shè)計(jì)師博雷克·西伯克工作。博雷克是歐洲三大設(shè)計(jì)師之一,在阿姆斯特丹和布拉格都有自己的工作室。“我也見證了布拉格在上世紀(jì)90年代初期的發(fā)展,它逐漸成為大家喜歡的旅游勝地。對于想體驗(yàn)歐洲文化的人來說,去布拉格非常經(jīng)濟(jì)實(shí)惠。”
當(dāng)被問及是否有搬回捷克的打算,斯泰潘指著腳下說:“我想過一段時(shí)間,但最終決定不回去。這里是我成長的地方、上學(xué)的地方,這里是家。”“我發(fā)現(xiàn),在捷克僑民中,存在兩種人:一種人喜歡朝前看,適應(yīng)了當(dāng)?shù)兀辛诵律睿灰环N人總是往后看,從來沒有停止過比較,一只腳還留在捷克。”他笑著說,“后一種人中,很多回國了。”
在西歐人眼里,東歐人的性格相當(dāng)矛盾。對此,斯泰潘是如何描述的呢?“捷克人免不了承受斯拉夫的憂郁和感傷,他們不是樂觀的人,這很容易理解。”他說,“幾個(gè)世紀(jì)以來,我們多次被入侵,二戰(zhàn)成為痛苦的集體記憶。當(dāng)?shù)聡{粹開始四處抓人的時(shí)候,我的父親才8歲。他們處決了我的爺爺,我的外曾祖母也是同樣的命運(yùn)。類似的事給捷克每一個(gè)家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”
面對任何一個(gè)渴望開始新生活的人,斯泰潘總是建議選擇荷蘭。他認(rèn)為,荷蘭社會秩序良好,人民自由溫和。“其實(shí),在上世紀(jì)60年代,荷蘭更開放、更寬容。我父親甚至在不會講荷蘭語時(shí),就得到了臨床心理醫(yī)生的工作,荷蘭為愿意努力工作的人們提供了機(jī)會。關(guān)于荷蘭,唯一需要批評的就是它的天氣。”他轉(zhuǎn)了一下眼睛說。
提到荷蘭民族精神的特點(diǎn),斯泰潘引用了兩句諺語,一句是“他在你的面前”,一句是“他不在嘴巴上放任何葉子”。后一句話是說,以前的演員經(jīng)常會拿一片無花果樹葉遮在臉上,從而保有一定程度的匿名性。用這句話來形容荷蘭人的直言不諱,真是再合適不過了,“嘴巴上不放樹葉”的荷蘭人一點(diǎn)也不覺得當(dāng)面批評有什么不妥。“當(dāng)然,荷蘭人也非常靈活,歡迎也愿意妥協(xié)。”他沉思了一下說。
當(dāng)問及什么書和電影有助于深化對荷蘭文化的理解,斯泰潘說:“我喜歡海拉特·雷弗的《黃昏》。二戰(zhàn)以后的生活就是那樣,今天還在影響荷蘭的精神。荷蘭語不是最優(yōu)美的語言,但是書里的荷蘭語非常優(yōu)美,這很不容易。”“還有一本書,我也非常欣賞——赫爾曼斯的《達(dá)摩克利斯的暗室》,盡管故事發(fā)生在荷蘭,但探討的問題是普世的。至于電影,我喜歡華麥丹的《阿寶》,反映了荷蘭社會的‘笨拙’和魅力。”
最后,斯泰潘深情地說:“希望荷蘭人能多一點(diǎn)浪漫,多一點(diǎn)非理性,不時(shí)做些瘋狂的事情。這將是我斯拉夫的憂傷的最好解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