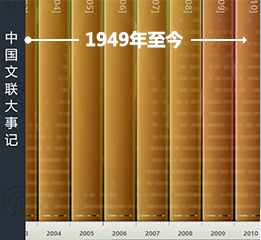黃永玉“戲論”藝術(shù)人生
“別太認(rèn)真看待我的畫,我的畫一點(diǎn)兒不嚴(yán)肅”

黃永玉觀看自己的畫作
這幾天,“黃永玉九十畫展”在國(guó)家博物館展出����。8月26日,剛舉辦過90歲生日會(huì)的黃永玉親臨展覽現(xiàn)場(chǎng)��,細(xì)細(xì)觀摩了自己的作品后��,與大家一起暢論了它們背后的故事�,以及多年來的人生感悟��,一句“別太認(rèn)真看待我的畫,我的畫一點(diǎn)兒不嚴(yán)肅”奠定了話題論調(diào)�����。
論意義:老先生走進(jìn)展廳時(shí)可謂健步如飛�����,引來很多人驚詫發(fā)問“那是黃老嗎”?展廳中的老先生一張張看得很仔細(xì)��,他說:“開展那天人太多��,沒有好好看?��!庇袝r(shí)邊看還邊自語道:“我畫過這張嗎?”
畫畫應(yīng)該開心�����、過癮�,一般來講���,我畫畫就是為了快樂、為了開心,實(shí)際上任何文化活動(dòng)都是開心的,比如說寫悲劇,那個(gè)作者本人也是開心的���,他不可能一邊流眼淚一邊寫,他控制這個(gè)作品,有創(chuàng)作的需求�����,畫畫也是一樣�。我這個(gè)人也沒有念過什么書���,也沒有正式地學(xué)習(xí)過,受過什么教育,所以我的這些畫畫技能都是撿來的����,東揀一點(diǎn)��,西揀一點(diǎn)�。要問最近我畫得開心的畫�����,我張張都開心,只有好與不好的區(qū)別��。有的畫掛出來我才知道原來我畫過這張畫、畫過那張畫。我天天畫��,記不得,人家問我說你有什么代表作,我說什么代表作����,我天天畫有什么代表作�����?有的人多少年畫一張畫,那才是代表作���。
一般來講,我不像有些很嚴(yán)肅的同志�,我這個(gè)人生下來就不怎么嚴(yán)肅�,一起床�����,不太討論今天生活的意義����,腳一下地���,穿上鞋��,主要就是想今天作品寫什么、怎么寫���,畫畫怎么畫���,沒有考慮這些東西莊嚴(yán)的意義���,一天到晚都是意義,不太好過日子����。
我這輩子沒有講意義,所以我就很難談到我要達(dá)到什么�����。我要是死了以后���,好朋友送到火葬場(chǎng)�����,把我燒成灰��,別人就回來,喝杯咖啡算了�,不要什么箱子裝骨灰����,什么道理呢�?作品也一樣�����,能留就留,不能留就別留了。活著的時(shí)候就好好地工作���,工作可能白干沒有價(jià)值���,也可能有點(diǎn)價(jià)值,不要把自己的意義看得太大����,我感覺我們活著有意思����、有趣就成了�,這輩子不是弄得很慘就可以了�����。
論創(chuàng)作:在第三展廳中�,懸掛著老先生一個(gè)月前才創(chuàng)作完成的最新作品《白描荷花》��,素雅的基調(diào)、丈二的尺幅�����,煞是惹眼��,這張用4天時(shí)間畫出來的畫,可謂老先生的“健康體檢表”���。
我為什么要畫荷花��?其實(shí)很簡(jiǎn)單,就是熟悉它而已���。小時(shí)候,我外婆家里荷花特別多�����,到了后來“文革”的時(shí)候�����,要了一張一丈二那么大的紙���,用厚紙把它卷起來,騎車子到圓明園那一帶畫荷花�����,為了逃避緊張的空氣��。還有一個(gè)是�����,荷花跟別的花不一樣,有花、有葉子���,還有底下的桿,有空間關(guān)系,所以,從第一張畫到第二張畫再到第三張畫��,都是技巧到技巧的表現(xiàn)���,覺得這方面的探索比較多�����。還有呢�,就是朋友�、熟人、社會(huì)上都喜歡我這方面的作品�,沒有什么深刻的道理�����。
我每天不一樣�,今天畫油畫�����,明天水彩,后天雕塑,都是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�����,有的事情畫畫解決不了��,要用雕塑來解決����,要用文字來解決�����。我不是正常培養(yǎng)的人�����,懂得比較多�����,就不受限制����,學(xué)校培養(yǎng)的人,有系統(tǒng)、有修養(yǎng)����,缺點(diǎn)是動(dòng)不動(dòng)就講系統(tǒng)��,美術(shù)學(xué)院就講素描���、講色彩,國(guó)畫一天到晚講筆墨����。不是不好,是你得有發(fā)展才行�����,不是變化創(chuàng)新��,而是要用另外的腦子來領(lǐng)導(dǎo)你的技能���,領(lǐng)導(dǎo)的本事沒有����,空有技巧���,就不好了�����。
我有一個(gè)想法����,文化活動(dòng)包括畫展����,多少年來形成了一個(gè)老習(xí)慣,書法就寫一寫古代詩人名家的語言�,畫畫就畫某一種畫。我常開玩笑說����,孔夫子說“吾少也賤,故多能鄙事”���。畫的題材也是一樣�,我更熟悉下層生活�����、最底層的生活,懂得他們的一些思維、語言,我希望展覽會(huì)上不是老用古人的話和詩詞,要在盡可能的范圍里面�,寫一點(diǎn)自己覺得開心的話�����。
論生活:雖然有點(diǎn)耳背����,但是老先生思維依然敏捷���,說話幽默、風(fēng)趣、睿智?�,F(xiàn)在很多人都感到壓力很大�,老先生卻仍保持著樂觀開朗的心態(tài),用快樂對(duì)付煩惱,畫畫與大家分享�����,應(yīng)是灑脫率直的個(gè)性使然�����。
在“文革”這么一個(gè)可怕的時(shí)代��,我居然玩得挺好��。人家問我為什么,我自己也想過,大概跟我的經(jīng)歷有關(guān)�����。我們小時(shí)候在鳳凰����,待兩天就看到一次殺頭�,看殺頭已經(jīng)看到了殺人的技巧有多高明的程度。到了抗戰(zhàn)八年,日本人在后面追����,我們?cè)谇斑吪埽w機(jī)在炸、大炮在轟�,死里逃生中度過的�����。12歲開始抗戰(zhàn),到了20歲抗戰(zhàn)勝利�����,長(zhǎng)大了�,這些就是我們自己的本錢。解放以后��,鍛煉了很多東西��,所以我在“文革”的時(shí)候特別能說謊��。有的同志很怕�,規(guī)規(guī)矩矩的��,從小到大��,沒見過這些�����,膽子小�����,我見得太多了�。拿破侖有一句話�����,“對(duì)待魔鬼要采取魔鬼的手段”���。我從來是往好處想,樂觀����、努力地去讓它變得正常,不正常也把它正?�;?/p>
一路走來好辛苦�����,因?yàn)闆]有基礎(chǔ)�����,書也沒有讀好,打地基打得很不結(jié)實(shí)�����。當(dāng)時(shí)是靠木刻培養(yǎng)自己���,有很多老前輩幫助我�����,大概覺得我這個(gè)年輕人尤其可愛�����,所以愿意幫助我吧。我自己也勤奮、努力�����、正派����,沒有去沾染那些不太好的東西。我的思想有點(diǎn)獨(dú)立��,有點(diǎn)自己的看法。那時(shí)肚子餓也好�����,衣服破也好,也高傲����,就是靠這個(gè)成長(zhǎng)起來的��。我留過好幾級(jí)��,說了很多人都不信��,上學(xué)的時(shí)間我干什么去了���?看書�����!課堂上的東西有限��。但現(xiàn)在不提倡年輕人像我這樣���,那就害了他們,首先要打好基礎(chǔ)。
經(jīng)歷過那么多時(shí)代���,現(xiàn)在最好�����!因?yàn)槿兆舆^好了����。那個(gè)時(shí)候十幾二十歲在上海,參加抗戰(zhàn)活動(dòng)�,那個(gè)年代很艱苦的,好不容易穿套西裝��,被國(guó)民黨的水龍頭一沖����,里面填充的草啊麻啊就散了�,回來放火上一烤燒沒了。老同學(xué)在念大學(xué)�����,在復(fù)旦�����、在同濟(jì),跑十幾二十幾里路去吃頓飯,然后再跑回來干活����,刻木刻���,自己拿錢��,自己找木板��,刻好交上去印傳單��。
用不著紀(jì)念那些悲傷��,干嘛要悲傷的負(fù)擔(dān)�。年輕人要過他們的日子��,為什么禮拜六、禮拜天要看《非誠(chéng)勿擾》呢�?就是這個(gè)道理,我要看他們是怎么對(duì)待世界的�、怎么思考的。你不要替他們擔(dān)心����,用你的角度來說這幫年輕人連什么人都忘了���,世界就是這樣的,我們老年人也要學(xué)習(xí)認(rèn)識(shí)年輕人。不過我這個(gè)人實(shí)在不行���,很原始的,電腦、電話我也不會(huì)����,人家問我我說我最擅長(zhǎng)的就是手電筒�,除了這個(gè)什么也不會(huì),不會(huì)利用現(xiàn)代化的工具,用的話就是聽音樂的唱機(jī),但是一個(gè)月沒回家了就需要重新學(xué)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