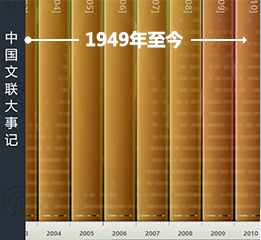沃土上的花繁葉茂,茁壯崢嶸,是何水法奉獻(xiàn)給時(shí)代的花鳥(niǎo)畫文本����,在這里�����,萬(wàn)物明媚����、萬(wàn)象燦爛,有限空間中映現(xiàn)的是一派大美圖景�,大美世界��。
他的“直視萬(wàn)象”,是一個(gè)由內(nèi)而外�����、再由外而內(nèi)的認(rèn)知與感覺(jué)過(guò)程����,是一個(gè)由學(xué)術(shù)傳統(tǒng)而引申出來(lái)的所思所行��,它漾溢著百年中國(guó)文化�����、藝術(shù)的靈魂演化脈絡(luò),從真正意義上達(dá)到了“借古而開(kāi)今”的新的學(xué)術(shù)境地����。
如果有一種繪畫是為了理想而畫�,是為了追求而畫,是面向未來(lái)而畫;那么,何水法的作品便是這樣的繪畫,并在一種身處“萬(wàn)象”中以“直視”的方式去實(shí)現(xiàn)���。

何水法
1946年8月生于杭州,1980年畢業(yè)于中國(guó)美術(shù)學(xué)院中國(guó)畫系花鳥(niǎo)畫研究生班。現(xiàn)為全國(guó)政協(xié)委員�,浙江省政協(xié)常委�,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���,中國(guó)美術(shù)家協(xié)會(huì)理事����,中國(guó)美術(shù)家協(xié)會(huì)中國(guó)畫藝術(shù)委員會(huì)委員,中國(guó)畫學(xué)會(huì)常務(wù)理事�����,浙江省特級(jí)專家��,浙江省美術(shù)家協(xié)會(huì)副主席�����,文化部中國(guó)藝術(shù)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�����、博導(dǎo)��,西泠印社理事,烏克蘭利沃夫國(guó)立藝術(shù)學(xué)院榮譽(yù)博士���,福建省畫院、福州畫院名譽(yù)院長(zhǎng)�,杭州師范大學(xué)美術(shù)學(xué)院名譽(yù)院長(zhǎng)�,洛陽(yáng)畫院名譽(yù)院長(zhǎng)�,洛陽(yáng)師范學(xué)院美術(shù)學(xué)院名譽(yù)院長(zhǎng),享受國(guó)務(wù)院特殊津貼專家����。
何水法曾對(duì)兩宋的花鳥(niǎo)畫作過(guò)精深的研究�����,其工筆花鳥(niǎo)畫結(jié)構(gòu)嚴(yán)謹(jǐn),用筆圓潤(rùn)自如,設(shè)色典雅秀逸��。寫意則受青藤��、八大之影響�����,氣旺神暢,筆墨華滋�����,渾然天成�����,厚實(shí)靈動(dòng)。
何水法作品被中國(guó)美術(shù)館����、中國(guó)國(guó)家畫院��、中央軍委、北京人民大會(huì)堂��、中南海紫光閣����、勤政殿、懷仁堂�、釣魚(yú)臺(tái)國(guó)賓館�����、美國(guó)亞洲藝術(shù)博物館���、日本國(guó)際美協(xié)�、澳洲東方藝術(shù)家協(xié)會(huì)����、烏克蘭利沃夫國(guó)立藝術(shù)學(xué)院等眾多機(jī)構(gòu)收藏。

青龍 140×376cm 2012年

十分春色 180×96cm 2012年
不是所有人都能躋身于歷史的���,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在歷史轉(zhuǎn)折點(diǎn)上。
何水法��,當(dāng)代中國(guó)花鳥(niǎo)畫家�,他的藝術(shù)獨(dú)創(chuàng)了當(dāng)代花鳥(niǎo)畫的新品質(zhì)、新境界���,而為世人所矚目��;60余年來(lái)��,藝術(shù)始終是他理想追求與價(jià)值表達(dá)的永恒方式。
作為一個(gè)純正學(xué)人式的畫家�����,他的藝術(shù)有一種深邃的東西����,那就是價(jià)值認(rèn)同方面的精神與立場(chǎng);以及對(duì)民族文化傳統(tǒng)的敬畏與反思�����,特別是對(duì)“筆墨當(dāng)隨時(shí)代”理念的認(rèn)知與踐行��;以及他的藝術(shù)風(fēng)格���、境界體現(xiàn)的“文化自覺(jué)”�����、“藝術(shù)回歸”與“學(xué)人情懷”;這不僅是他個(gè)人識(shí)見(jiàn)或人生選擇�����,也表征了一代藝術(shù)家對(duì)民族文化精神歷程的共同認(rèn)知與凝重審視���。
整體而言���,何水法是一位鐘情于文化精神��、熱愛(ài)大自然、敬畏生命的抒情畫家��,而筆墨的清麗�����、氣息的典雅���、品格的高蹈��、情調(diào)的明朗、意蘊(yùn)的雋永悠長(zhǎng),映照出的是畫家及其時(shí)代的豐饒與遼闊��。
數(shù)十年的藝術(shù)歷練�,畫家以生命和藝術(shù)的徹悟,抵達(dá)了豁然開(kāi)朗之境,獨(dú)創(chuàng)了一代畫風(fēng)��,卓然而立于當(dāng)代畫壇�����;在事實(shí)上��,他把當(dāng)代寫意花鳥(niǎo)畫推向了眾所矚目的高度。
一
古今中外經(jīng)典作品���,無(wú)一不是生命和語(yǔ)言同時(shí)抵達(dá)的超然之境�。
何水法近年的一系列作品�����,日益顯示出其藝術(shù)的深思熟慮與爐火純青���,作品中的花鳥(niǎo)意象已不再簡(jiǎn)單地抒寫視覺(jué)之美��,他要構(gòu)建的是自成體系的藝術(shù)世界��,并在其中凝聚了自己的情感意緒與價(jià)值取向��,在漸次沉淀與提升中,抵達(dá)了藝術(shù)本質(zhì),呈現(xiàn)出具有本質(zhì)性的深長(zhǎng)意味��,并在付諸筆墨后展現(xiàn)為淋漓酣暢���、形神兼?zhèn)渑c氣韻生動(dòng)的自然生命形式和自然生命景觀�。
直視萬(wàn)象。既是一種心態(tài),又是一種襟懷,還是一種體察世界的方法�����;何水法的作品以“直視萬(wàn)象”為特點(diǎn)��,強(qiáng)調(diào)文化意蘊(yùn)的傳達(dá)�����,同時(shí)也注重筆墨過(guò)程與精微細(xì)節(jié)的展示,如其作品《云錦》���,在不同筆型、筆法的書寫中使花卉枝條��、藤蔓���,在粗細(xì)大小��、干濕濃淡��、意到筆不到、形斷意連中呈現(xiàn)出交叉����、回旋�、恣肆以及集束與擴(kuò)散�����,而又茁壯崢嶸中的蓬勃旺盛生機(jī),以線條為主的畫面在看似無(wú)序的紛繁復(fù)雜交織中���,統(tǒng)歸于整體的有序,并在一種伸展與聚攏的空間位置中�,呈現(xiàn)張力��,這是感性生動(dòng)生命形式的勃發(fā)與表現(xiàn);筆力則在意象生命的生機(jī)與氣韻上著力�,在中鋒���、側(cè)鋒���、逆鋒��,乃至回旋往復(fù)中,體現(xiàn)書寫之美���、節(jié)奏之美、韻律之美與力度之美��,因此���,作品含量倍增��;因?yàn)椤爸币暼f(wàn)象”��,畫家強(qiáng)調(diào)的是一種畫面“感覺(jué)”的營(yíng)造,是一種“物象”真實(shí)到“意象”想象的轉(zhuǎn)化與提升,是自然生命的蓬勃感和對(duì)生命生動(dòng)形式的感受����、發(fā)現(xiàn)與提取�。由此,讓人在文化聯(lián)想中���,產(chǎn)生思接千載��、視通八荒的廣闊與宏大的幻覺(jué)�����,可以看出,畫家的關(guān)注點(diǎn)在于拓展作品中有限意象的想象空間����,并從中直入自然生命本質(zhì)����,追尋內(nèi)在生機(jī)���,在感覺(jué)中凝聚與結(jié)晶意象�,而非花卉、鳥(niǎo)蟲(chóng)的外在形態(tài)���,這樣的直視——直覺(jué)感受方式,反因重在生機(jī)氣韻的營(yíng)造而顯出整體的自由靈動(dòng)與渾然,如《云錦》《金鳳》《凌云》《曼陀羅》《湖上所見(jiàn)》《紅芳擎艷》等�,亦因此在生命的勃勃欲發(fā)中��,平添了搖曳多姿的神采風(fēng)骨,這與時(shí)下流行的艷俗與淺薄短見(jiàn)的作品判然有別;同樣的,畫家在作品中無(wú)意于以“植物學(xué)”眼光去考據(jù)花鳥(niǎo)的意象真實(shí)與否,亦無(wú)意論證某種花卉品種入畫后是否合乎情理�,而是在直覺(jué)的把握中將錯(cuò)就錯(cuò)���,不計(jì)正謬曲直���,追求感覺(jué)中意象的模糊���、虛擬與不確定性�,以及在相對(duì)性中的生命蘊(yùn)含���、書卷氣息�����,并對(duì)其進(jìn)行深入挖掘和獨(dú)特闡發(fā),在“以情舍理”中完成豐富的聯(lián)想和內(nèi)在理趣的想像性寫意表現(xiàn)。
因此�,以“直視萬(wàn)象”為特點(diǎn)的何水法花鳥(niǎo)畫�,無(wú)一不是在神與物游����、觀物取象中,意從象出���,并在化實(shí)為虛的形神機(jī)趣中,融入了“情深而文明���,氣盛而化神”的品格,在“氣之動(dòng)物����、物之感人�,故搖蕩性情”的狀態(tài)中��,使內(nèi)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運(yùn)動(dòng)生機(jī)���,感應(yīng)并相互關(guān)聯(lián)���,讓充實(shí)之美與意氣駿爽的清焉文風(fēng)充盈于畫面�����,因此,才得以使有限畫面轉(zhuǎn)化為無(wú)限空間,實(shí)現(xiàn)“以小見(jiàn)大”、“以技入境”的提升與伸展�����,據(jù)此��,何水法一掃花鳥(niǎo)畫傳統(tǒng)的狹隘�����、單調(diào)格局與凄清冷落的美感,而直入氣宇非凡�、至大至剛的壯闊浩蕩境界���,使之“暉麗萬(wàn)有”��,而別具風(fēng)神韻致。
直視�����,是藝術(shù)現(xiàn)代性的重要觀察與思維方式����,它不做邏輯的推演與實(shí)證分析,它重在對(duì)物象“不真實(shí)的把握”�����,以及在客觀規(guī)律之外和邏輯秩序之上另尋蹊徑���,并在融入虛擬性��、夸張�����、變形與想象和刪繁就簡(jiǎn)中創(chuàng)造詩(shī)化特征,最終�,凝煉為感性生動(dòng)的生命形式。
從直覺(jué)出發(fā)��,經(jīng)由某種感覺(jué)����,然后直視萬(wàn)物萬(wàn)象,在當(dāng)代文化語(yǔ)境的八面來(lái)風(fēng)與紛繁多變中���,讓感性生動(dòng)的生命形式及其郁勃生機(jī)、風(fēng)采��,充實(shí)并成就花鳥(niǎo)畫文本構(gòu)建與精神詮釋����,并在“觀山則情滿于山,觀海則情溢于?�!钡那樗贾?����,使作品直抵經(jīng)典藝術(shù)高度與完美詮釋���。
二
沃土上的花繁葉茂���,茁壯崢嶸��,是何水法奉獻(xiàn)給時(shí)代的花鳥(niǎo)畫文本,在這里�����,萬(wàn)物明媚�����、萬(wàn)象燦爛,有限空間中映現(xiàn)的是一派大美圖景,大美世界。
對(duì)何水法的藝術(shù)關(guān)注�,始于當(dāng)代中國(guó)畫����、特別是花鳥(niǎo)畫在當(dāng)代發(fā)展遭遇的困境��,在普遍疲軟��、激情衰頹的情勢(shì)下�����,何水法以其文化風(fēng)骨和旺盛的創(chuàng)作活力登場(chǎng),并以他那一代人中罕見(jiàn)的功力、靈性與直視萬(wàn)象的風(fēng)采���,成為眾人中的異數(shù),頗有“眾人皆醉我獨(dú)醒”的意味����。
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���。
祖籍紹興�����,生于杭州的何水法,深得江南文化的浸潤(rùn)與陶冶���,沉厚傳統(tǒng)文化的潛移默化與耳濡目染,以及豐富的人生閱歷帶給他的是感悟力���、觀察力與現(xiàn)實(shí)感受的敏銳和藝術(shù)觀念的自覺(jué)。畫家早在十三四歲時(shí)始臨瘦金體書,稍后�����,又臨習(xí)鐵線篆和《石門頌》《乙瑛碑》《禮器碑》等碑帖����,以及顏真卿��、文徵明�����、伊秉綬諸家書法,深得筆法�����、筆勢(shì)與筆力的奧秘與玄機(jī)����,其時(shí)他小小年紀(jì),書法篆刻作品便多次參展與發(fā)表了,顯露出“青出于藍(lán)而勝于藍(lán)”之銳氣�;至20世紀(jì)60年代初�,遂開(kāi)始以工筆花鳥(niǎo)為課題專攻���,起初由宋人花鳥(niǎo)入手�,在研究、臨習(xí)兩宋花鳥(niǎo)作品的基礎(chǔ)上與寫生結(jié)合���,此時(shí),作品已顯現(xiàn)出形神兼?zhèn)?�,氣韻生?dòng)的風(fēng)采�����,在日復(fù)一日���、年復(fù)一年的苦苦求索與不倦筆耕中,藝術(shù)鋒芒初露�����,令人刮目;因此�,深受彼時(shí)大家陸抑非���、陸儼少�、吳茀之�����、謝稚柳��、唐云�����、陸維釗、沙孟海的賞識(shí)與青睞�,當(dāng)他在1987年考上浙江美術(shù)學(xué)院陸抑非教授花鳥(niǎo)畫研究生班后�,深得名師再傳�����,其藝術(shù)風(fēng)格亦漸由陸抑非上溯到前人惲南田一脈���,筆墨之間溢出清朗雋秀��、幽雅淡疏之情調(diào),頗得前人筆致意韻���,以脫盡縱橫習(xí)氣轉(zhuǎn)為澹然天真的靜�、凈之風(fēng),苦讀數(shù)度春秋��,得由表及里之真諦���,領(lǐng)悟了工筆花鳥(niǎo)畫之真髓��,間或于由工入寫���,達(dá)工而不工�����,兼工帶寫、工寫兼具的跨界表現(xiàn)�,遂產(chǎn)生循序漸進(jìn)與日益深入的提升��,名師高徒,此期間����,依導(dǎo)師指點(diǎn)��,以壯游寫生為基礎(chǔ),且以瘦金書法入畫�,筆致漸生銀鉤鐵劃之力度與神韻��,形成工而不滯、骨體蒼勁��、結(jié)構(gòu)嚴(yán)謹(jǐn)與圓潤(rùn)自如的風(fēng)神格體�����。
工筆花鳥(niǎo)畫的堅(jiān)實(shí)基礎(chǔ)����,為隨后向?qū)懸饣B(niǎo)畫轉(zhuǎn)型�����,奠定了雄厚的技術(shù)準(zhǔn)備。在陸抑非先生指導(dǎo)下,何水法開(kāi)始了由工筆向?qū)懸獾倪^(guò)渡,大量寫生的技術(shù)與造型積累�,使他對(duì)花卉結(jié)構(gòu)��、規(guī)律了然于心,在厚積薄發(fā)中,由工入寫����、工寫融通�����,他走上了更為情緒化、更具個(gè)性特點(diǎn)的藝術(shù)之路。
許是秉性使然,在放筆直抒、墨色并用的寫意花鳥(niǎo)畫中��,何水法漸漸消解了純技術(shù)的物性表達(dá)����,畫面在渾厚華滋與酣暢淋漓中漸顯出一派新意����。陸儼少先生評(píng)價(jià)何水法此時(shí)的作品說(shuō):“可醫(yī)近世無(wú)根少蒂之病�。”
此后,何水法花鳥(niǎo)畫日趨走向大格局,所做花鳥(niǎo)畫不論大小,均體現(xiàn)為大氣象與大境界�;顯然�,古今書畫大家的書寫體勢(shì)與筆勢(shì)����,特別是徐渭、李復(fù)堂、吳昌碩����、任伯年等的作品及藝術(shù)經(jīng)驗(yàn)�����,成為他的楷模與滋養(yǎng)���。前人藝術(shù)的渾古風(fēng)格����,拓展了中國(guó)畫前所未有的境界,他們那種書畫俱老���,爛漫天成而無(wú)頹唐氣象,以及剛而能柔���、老而滋嫩、蒼而含潤(rùn)��,古而生秀的畫風(fēng)���,給了何水法以花鳥(niǎo)畫寫意的靈性��、品格與胸懷的啟示���,使他在依自然開(kāi)合的取勢(shì)中完成了謀篇�����、布局與造勢(shì),特別是在筆勢(shì)的縱橫與起承轉(zhuǎn)合中����,生發(fā)出不窮之意�,使他得以在宏觀上把握萬(wàn)物運(yùn)動(dòng)規(guī)律��,并在萬(wàn)物萬(wàn)象的不分巨細(xì)“無(wú)往非開(kāi)合也”的生命運(yùn)動(dòng)形態(tài)中,獲得花鳥(niǎo)畫生命形式與精神氣韻表現(xiàn)的依據(jù)�����。
細(xì)讀何水法的寫意花鳥(niǎo)畫��,不難看到���,鴻篇巨制也好��,咫尺小品也好,畫面的布局章法和景物勢(shì)態(tài)的安排處理���,莫不以體現(xiàn)宇宙萬(wàn)物開(kāi)合聚散的運(yùn)動(dòng)變化方式為特點(diǎn),即畫面每每為大開(kāi)大合與對(duì)角線式的攀升騰躍��,以及上下呼應(yīng)的起伏跌宕的構(gòu)圖��,或令人觸目驚心����,或令人直上云端……��,因此�,既是錯(cuò)綜紛呈的���,又是有序展開(kāi)的�。自20世紀(jì)末,何水法花鳥(niǎo)畫作品漸漸以全景式構(gòu)圖布局呈現(xiàn),亦如山水畫之高遠(yuǎn)����、深遠(yuǎn)���、平遠(yuǎn)�,并運(yùn)用其團(tuán)塊式結(jié)構(gòu)產(chǎn)生“欲俯先仰、欲重先輕����、欲放先收”和“先須相勢(shì)”�、“先欲一氣團(tuán)煉”的錯(cuò)綜起止之勢(shì)�,使花鳥(niǎo)畫頓生如山水畫那樣把握云氣煙嵐整體意象的大景觀。
清人鄒一桂在《小山畫譜》中說(shuō)�����,“章法者,以一幅之大勢(shì)而言��。幅無(wú)大小,必分賓主��。一虛一實(shí)�����,一疏一密��,一參一差�,即陰陽(yáng)晝夜消息之理也���?�!髣?shì)即定����。一花一葉亦自有章法���?�!碑?dāng)這一切訴諸筆墨意趣與形式結(jié)構(gòu)時(shí)��,在滿紙惠風(fēng),花枝燦爛之中��,體現(xiàn)的正是“有所承接而來(lái)���,有所脫卸而去”(沈宗騫語(yǔ))的簡(jiǎn)約與形式秩序的把握和對(duì)事物節(jié)奏��、韻律的理解����,并借用“即山川而取之��,則山水之意度見(jiàn)矣����;真山水之川谷���,遠(yuǎn)望之以取其勢(shì)�����,近看之以取其質(zhì)”入花鳥(niǎo)畫的構(gòu)思����、章法�、布局,使一幅咫尺花鳥(niǎo)畫陡生高山流水���、重巒疊嶂之磅礴氣象,盡生大氣流貫���、渾然蒼茫之感,移山水畫之勢(shì)入花鳥(niǎo)畫是何水法先生首創(chuàng)�,當(dāng)為一大創(chuàng)舉��。
“致廣大與盡精微”,在畫家作品《耀春》《赭蘭》《春風(fēng)拂檻》《黃瓜》《引蔓出云》《一串紅映萬(wàn)里霞》《映紅》《凝紅》《黃葉近秋風(fēng)》《紺架垂垂籠紫霧》《層林盡染》《霞艷》《新綠成蔭》《紅芳擎艷》《凌云》中���,都因?yàn)槠鋱F(tuán)塊結(jié)構(gòu)和移山水畫之勢(shì)入花鳥(niǎo)畫結(jié)構(gòu),以及幾根枝條的攀爬��、走勢(shì)與花朵怒放的形態(tài)��、韻致�����,讓人聯(lián)想到“山外有山,雖斷而不斷����;樹(shù)外有樹(shù)��,似連而非連”的山水架構(gòu)與氣象,畫面上的花鳥(niǎo)意象����、點(diǎn)線�、墨色都有或隱或顯的如山石���、樹(shù)木般的脈絡(luò)聯(lián)系�,使之雖為花鳥(niǎo),卻顯示為虛實(shí)相生般的峰巒疊嶂式的險(xiǎn)峻�、巍峨���、曲折�、深幽�����,使之既富有層次與動(dòng)感,又在布局與筆勢(shì)中見(jiàn)出萬(wàn)物萬(wàn)象的生命氣脈�。
上述作品����,因而產(chǎn)生“遠(yuǎn)觀則氣勢(shì)撼人�����,近看則驚心動(dòng)魄”的效果����,使花鳥(niǎo)作品�,壁壘森嚴(yán)又氣勢(shì)磅礴,危崖陡峭又疏朗靈動(dòng)�����,滿紙惠風(fēng)�����,花枝燦爛�,大氣流貫��,浩蕩蒼茫�,氣象取勢(shì)因而有別于一般����。稍加注意,便能發(fā)現(xiàn)�,畫面整體大勢(shì)與局部的靈動(dòng)虛空��,是完美結(jié)合的��,花卉主干的干裂秋風(fēng)或潤(rùn)含春雨��,與恣肆筆法�、皴擦�����、復(fù)筆���,乃是在“朽定大勢(shì)”中����,落墨并各隨其便的�����,且自得血脈貫通而渾然一體�,其中筆墨隨畫面走勢(shì)而氣旺神暢�,顯見(jiàn)其中的豪宕之力乃源于布勢(shì)的奇崛與起伏,進(jìn)而確定了筆意墨韻的“各隨其便”的揮灑自由���。“以氣勝得之者�,精神燦爛”�,何水法作畫����,以氣勝得之,故以氣運(yùn)筆,筆力遒勁���,墨色渾厚華滋,既有寫意的灑脫風(fēng)神,又見(jiàn)筆墨書寫之沉厚雋永意趣。
作于1999年的《映紅》����、2001年的《映紅》與《一串紅映萬(wàn)里霞》,作為代表性作品�����,可以見(jiàn)出何水法筆無(wú)妄下的老到�����、瀟灑與縝密�、嚴(yán)謹(jǐn)���;畫面意象在極盡夸張與取意之中����,以滿密、繁復(fù)見(jiàn)長(zhǎng)���,在近乎西方構(gòu)成意識(shí)的幾何或空間布局中,以紅�、黑兩大色塊對(duì)比為主�,演繹出畫面緣于“勢(shì)之凝聚”而產(chǎn)生的跌宕�、起伏、沖突與張力��,在沉穩(wěn)與厚重中��,積蓄著相對(duì)性與不確定性��、積蓄著熱烈的意緒和高昂的情調(diào),讓人在一種躍動(dòng)中產(chǎn)生非同尋常的視覺(jué)刺激�,且在見(jiàn)仁見(jiàn)智的理解中�,各得其所�����,久久難忘。
1999年《映紅》到2001年的《映紅》����,可以看出藝術(shù)上的循序漸進(jìn)和遞次深化���,時(shí)間跨度雖短���,筆墨卻日見(jiàn)精煉老到���,色彩愈見(jiàn)沉厚脫俗�,文本特征日趨個(gè)性化、情緒化和大開(kāi)大合的“萬(wàn)象在旁”之氣派�;2001年的《映紅》�����,在滿密繁復(fù)中見(jiàn)出虛靈,墨色相諧艷而不俗����,妖嬈中又見(jiàn)含蓄��,干濕濃淡之間營(yíng)造了虛實(shí)相生的不息生機(jī),枝條的穿插����,既造成了空間關(guān)系的多樣與豐富�,又見(jiàn)出若即若離間的筆墨之自由境地���,畫家在極妍盡態(tài)中的精湛運(yùn)思與氣象圓融躍然紙上��;從1999年到2001年���,以同一主題創(chuàng)作的《映紅》,是“同中有異”的,表明的是畫家的日見(jiàn)老到成熟與日臻爐火純青的藝術(shù)高度與深度���;何水法的近作,尤見(jiàn)在“妙心所發(fā)”中��,形成物我相合��、心手兩忘���、興會(huì)淋漓的圓融之境����,在點(diǎn)線交織���、點(diǎn)色綴墨�,虛實(shí)相間、逸遠(yuǎn)疏澹中���,畫家得以在法度與自由中,別開(kāi)了花鳥(niǎo)畫的生面與獨(dú)創(chuàng)一代新風(fēng)�。
在其他作品中����,如《金光》《芙蓉》《紅梅綻放》《紅芳擎艷》《湖上所見(jiàn)》《凌云》《云綻霞鋪》《自落自花還自香》《笑迎秋露》《海棠花放艷秋光》等�,均體現(xiàn)出何水法一貫的熱烈、豐饒與飽滿的畫風(fēng)��,畫家秉承了前賢吳昌碩的“畫氣不畫形”的理念�����,以寫“高曠之氣”為目標(biāo)��,抒寫粗野樸茂的生命元?dú)猓蛔鳟嬛校蝗沃饔^抒寫,不拘泥于象�,而直入“郁勃縱橫氣象”之內(nèi)在����,同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又在整體的團(tuán)塊式文本結(jié)構(gòu)中,在戈戟森歷、生拗橫肆的如篆用筆中,不乏飄逸空靈��、清秀疏淡的點(diǎn)線盤亙周邊���,兩者相攜���,體現(xiàn)了象中取意���,在意中生發(fā)情緒并抵達(dá)交融�����,在內(nèi)涵豐富與多樣的演繹幻化中��,形成新體�����,畫家的審美取向與藝術(shù)風(fēng)致則在此中氤氳而來(lái);就此而言,說(shuō)何水法續(xù)寫了花鳥(niǎo)畫創(chuàng)作新格之典范與書寫了花鳥(niǎo)畫史新篇章,是毫不過(guò)分的����。
何水法是一位從容優(yōu)游的“天懷浩落者”(唐符載《取勢(shì)》語(yǔ))����,其作畫往往“一筆開(kāi)之”而不可收拾��,常常“時(shí)至興來(lái)”、“片時(shí)妙意”,信筆揮灑,并因此產(chǎn)生諸多情緒熾烈、韻致生動(dòng)的絕佳之作。細(xì)讀如《青藤》《曉露紅芳》《聽(tīng)濤聲麟髯夜怒》《誠(chéng)齋詩(shī)意》《艷紅》《金露》《蒙茸萬(wàn)縷紫玉英》等作品��,但見(jiàn)其如萬(wàn)歲枯藤式的用筆�,雖粗礪霸悍又深得金石意味,卻在茁壯中見(jiàn)生機(jī),游刃有余與遒勁蒼茫���,恣肆放逐卻有分寸的行筆變化,行滯之間皆見(jiàn)騰挪變幻����,在信筆橫掃中����,悉心掌控節(jié)奏���、韻律與力度���,在運(yùn)筆中強(qiáng)調(diào)重���、拙��、大的園勁嚴(yán)峻��、恣肆沉穆,剛?cè)嵯酀?jì)���,而以書法筆致入畫,運(yùn)于章法��,則有回綰之勢(shì)�����,一如狂草筆致���,增加了渾古之力和本色之美;其次��,借助干濕濃淡的互動(dòng)與演繹���,營(yíng)造粗糲����、金石意味中的靈動(dòng)、飄逸與疏朗感��,在實(shí)處更實(shí)�����、虛處更虛����、黑處更黑�����、淡處更淡��、密處更密中��,折射出自然生命秩序的內(nèi)在生機(jī),并造成參差錯(cuò)落�,萬(wàn)象崢嶸的生命活力與郁勃之感����,這已成為何水法花鳥(niǎo)畫的鮮明特點(diǎn)�。古人說(shuō)“欲得勢(shì),必先培養(yǎng)其氣”�����,何水法執(zhí)筆����,乃先醞釀“心腕之靈氣”�����,調(diào)動(dòng)平日之藝術(shù)修養(yǎng)�����,力求使自我主觀精神、精神視野合乎高層次詩(shī)意化的藝術(shù)創(chuàng)造要求,使之達(dá)于心胸,而靈氣充溢也;其次����,是胸中郁勃與天地之氣�,相合于筆墨技巧�����,使主體精神�、藝術(shù)追求�、審美理想與靈感相融通,而至完美與爐火純青的境界�����,由此展示出以技入境的渾然天成的筆墨品質(zhì)與格調(diào)�����。
在“灑然出之����,有自在流行之致��,回旋往復(fù)之宜,不屑屑以求工���,能落落而自合”的得心應(yīng)手如《二月花放春如海》《紅梅賦》《洛神春賦》等巨幛中����,何水法用色的獨(dú)到����,高人一籌��,平添了畫面勃勃欲發(fā)之勢(shì)���,使意象頗具“心花怒放�����,筆態(tài)橫生”之神采;在色不礙墨、墨不礙色中���,色墨交互輝映,使畫面生機(jī)四溢,盡顯活力。與此同時(shí),他以勾勒之筆法用色,多敷染�����、點(diǎn)染、烘托、潑彩等�,并在主色中調(diào)以花青��、淡墨,降低其純度,使之艷而不燥���,麗而不火��,達(dá)到清麗典雅潤(rùn)澤的效果����;在用色中���,畫家極力營(yíng)造層次感�����,落色于畫面時(shí)�,注意與宣紙�、點(diǎn)線、筆墨�����,意象之間的滲化與互補(bǔ)�����,形成空間關(guān)系���,使花朵在燦如云霞中演繹出一種意味深長(zhǎng)的氤氳之美���,臻于化境���。
從傳統(tǒng)中脫穎而出���,必然面對(duì)一個(gè)取向的選擇問(wèn)題��,任何人都難以回避���;何水法則強(qiáng)調(diào)在研習(xí)傳統(tǒng)中轉(zhuǎn)化它��,使之成為一種精神而綿長(zhǎng)延展下去�,進(jìn)而在執(zhí)筆揮毫之際�,于不易察覺(jué)中,漸漸沉淀為“情感流露”�、“生命軌跡”����,因此��,當(dāng)筆墨在紙上喚風(fēng)呼雨的剎那�����,一切顯現(xiàn)筆端。
就此而言����,何水法花鳥(niǎo)畫的獨(dú)創(chuàng)性及其文化意蘊(yùn)���,是許多同代人難以比肩的����;因?yàn)?����,他始終不渝地強(qiáng)化與專注于作品的學(xué)術(shù)性�����、研究性和藝術(shù)的內(nèi)涵,并在此中抵達(dá)藝術(shù)的深處。
而《鳳凰花》《輕逗一片》《芳溪春色》《土耳其所見(jiàn)》《馬塞馬拉所見(jiàn)》《花氣上天香作云》《鳶尾》《跳舞蘭》等作品����,均為他訪游他國(guó)的自然風(fēng)物所見(jiàn)�����,這些出自不同地域、不同國(guó)家的植物��、花卉��,在何水法筆下體現(xiàn)出中國(guó)畫筆墨的原創(chuàng)性�����,雖為點(diǎn)、線����、墨���、色的運(yùn)用���,卻見(jiàn)出奇瑰與新穎的創(chuàng)意��;而對(duì)鮮見(jiàn)的異國(guó)花卉,既無(wú)前人經(jīng)驗(yàn)可以借鑒,又無(wú)當(dāng)代人的作品可參照,在莫言文集所作的《紅高粱》《蒜薹》《蛙聲》《透明的紅蘿卜》以及水墨小品《雙芋》《鳳尾竹》《清音》《此中有真味》���,他在傳統(tǒng)經(jīng)驗(yàn)與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的雙重經(jīng)驗(yàn)積累中,原創(chuàng)性地提取了意象形態(tài),在刪繁就簡(jiǎn)中��,運(yùn)用枯�����、濕、濃��、淡的筆墨形態(tài)�,發(fā)揮筆、墨�、色����、水的綜合性能與優(yōu)勢(shì)�,使之在形神、氣韻方面都達(dá)到生動(dòng)、蓬勃與清新����、悅目與典雅���、豐富而神奇的藝術(shù)效果�。
由此����,不難看出,何水法直視萬(wàn)象���,抵達(dá)藝術(shù)的旖旎深處,并表現(xiàn)為一種從容自然的狀態(tài)����,在生命與藝術(shù)同在的狀態(tài)之中��,傾訴著內(nèi)心的情感,這樣的藝術(shù)創(chuàng)造�,孕育并產(chǎn)生于對(duì)萬(wàn)象的直視��,及對(duì)萬(wàn)物生命的體悟與熱愛(ài)。
何水法的花鳥(niǎo)畫藝術(shù)�,愈至晚近����,愈發(fā)清峻老到����,在風(fēng)神勁爽中刷新著歷史的塵埃�,作品漾溢著特有的清新、豐贍�、純正與靈動(dòng)感����,這一切表明,當(dāng)一個(gè)人以靈性的感覺(jué)直視萬(wàn)象時(shí)���,那筆墨定然是有奇力的,當(dāng)藝術(shù)靈魂一旦回到筆下�,便會(huì)不自覺(jué)地走進(jìn)重新孕育的過(guò)程��,并生成一種建構(gòu)性的巨大力量。
三
何水法生活的時(shí)代�����,是轉(zhuǎn)型與巨變的時(shí)代�����,這一進(jìn)程中的總體態(tài)勢(shì)���,使中國(guó)畫面臨著由傳統(tǒng)向現(xiàn)代的艱難過(guò)渡��,也折射出郁積多年的求新求變的學(xué)術(shù)期待——找到全新的藝術(shù)突破點(diǎn)和理論支點(diǎn)。
在這個(gè)背景中���,何水法花鳥(niǎo)畫藝術(shù)的成熟與突破,起著“一石激起千層浪”的先行意義�,也表征著新中國(guó)畫的一個(gè)腳踏實(shí)地的演進(jìn)方向��,與此同時(shí),長(zhǎng)期以來(lái)的必然性結(jié)構(gòu)和歷史循序漸進(jìn)的推演被撼動(dòng)了���;何水法的藝術(shù)����,讓我們得到了這樣的啟迪——在延伸傳統(tǒng)連續(xù)性的同時(shí),還要發(fā)現(xiàn)其內(nèi)在的裂變�����,在看似復(fù)雜的時(shí)代情勢(shì)中�����,要善于看到轉(zhuǎn)折與可能性��,并使之成為創(chuàng)新的機(jī)遇,成為反抗歷史異化的力量�。
實(shí)踐表明���,堪稱卓越的作品�����,必然地具備想象力,洞察力和原創(chuàng)能力,它們乃是作品成功的核心所在�����。何水法在上述三者的支撐下��,依托長(zhǎng)期的藝術(shù)的�����、學(xué)術(shù)的積累���,遵循著——回到藝術(shù)的運(yùn)行�����、演進(jìn)的實(shí)際過(guò)程中����,回到藝術(shù)發(fā)生�����、變異�����、變革的具體環(huán)節(jié)中���,回到藝術(shù)形式結(jié)構(gòu)的內(nèi)在質(zhì)地的規(guī)律中�����,因此,得以在一個(gè)高度上觀瞻中國(guó)畫精致優(yōu)美的結(jié)構(gòu)形態(tài)和氣象風(fēng)神,以及生命情狀與情感體驗(yàn)�����,這是一個(gè)非物性�����、非實(shí)證化的視角,從這點(diǎn)出發(fā)�,看待自然與生命�,便能每每超越現(xiàn)實(shí)語(yǔ)境�����,憑借審美高度和感覺(jué)的敏銳�����,捕捉到萬(wàn)物的生命姿態(tài)和萬(wàn)象的鮮活氣息。
與此同時(shí)�,在充盈了物性與精神性的積累中��,畫家始得以毫不動(dòng)搖地堅(jiān)守著詩(shī)意化的理想和詩(shī)意化的精神家園。何水法的藝術(shù)���,在“筆墨能與造化通”之中,營(yíng)造出撥動(dòng)人心的美感與魅力��,這是因?yàn)?����,他自覺(jué)地把生命精神����、心靈融入大自然無(wú)盡的循環(huán)和更新的節(jié)律之中��,在心無(wú)旁騖中營(yíng)造自我的精神的審美之境��,而且他的藝術(shù)隨著人生歷程遞進(jìn)不斷呈現(xiàn)出有機(jī)生長(zhǎng)的勢(shì)頭與狀態(tài)——?dú)鈩?shì)恢宏又開(kāi)闊深邃,筆墨老到又別開(kāi)生面�;他一邊秉承獨(dú)抒性靈的傳統(tǒng)����,一邊又緊密關(guān)聯(lián)著萬(wàn)物萬(wàn)象內(nèi)在的郁勃機(jī)制�;所以�����,何水法的藝術(shù)從未泯滅永恒的藝術(shù)追求�,而文化精神的深厚與意義����,藝術(shù)情思的價(jià)值與意義,正蘊(yùn)含在他作品特有的充實(shí)���、豐腴、飽滿與絢爛意象之間�。
環(huán)顧當(dāng)代畫壇���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何水法有著多方面的意義���,在藝術(shù)求索上�����,他是一個(gè)勃發(fā)與沉潛�、熱情與認(rèn)真�、投入與超越同時(shí)兼?zhèn)涞膶W(xué)人式畫家,是承前啟后的典范�����,顯示出“士能弘毅方能致遠(yuǎn)”的品格��;在藝術(shù)過(guò)程中����,他充分吮吸傳統(tǒng)精神乳汁��,并將對(duì)“萬(wàn)象”的關(guān)注納入藝術(shù)觀察與感受的視野,力避形而下思維所限制的藝術(shù)視野的深與廣��;在藝術(shù)精神上���,他坦然接受一個(gè)學(xué)人式畫家所必然面臨的挑戰(zhàn):堅(jiān)守自己�����,知難而進(jìn)�����、不倦開(kāi)拓,辛勤耕耘,自強(qiáng)不息���,以自己獨(dú)有極具個(gè)性化的藝術(shù)建樹(shù)參與當(dāng)代美術(shù)史的創(chuàng)建與書寫。
何水法的藝術(shù)之路,雖然并非一帆風(fēng)順����,卻又行走得特別堅(jiān)實(shí)與純粹�。
他的“直視萬(wàn)象”���,是一個(gè)由內(nèi)而外�、再由外而內(nèi)的認(rèn)知與感覺(jué)過(guò)程,是一個(gè)由學(xué)術(shù)傳統(tǒng)而引申出來(lái)的所思所行���,它漾溢著百年中國(guó)文化、藝術(shù)的靈魂演化脈絡(luò)���,從真正意義上達(dá)到了“借古而開(kāi)今”的新的學(xué)術(shù)境地。
“傳統(tǒng)還是創(chuàng)造”�?是何水法存在的現(xiàn)實(shí)���,古人與前人的藝術(shù)經(jīng)驗(yàn)與精神資源����,對(duì)何水法而言�,乃是一種激活與曾有的脈動(dòng)與體溫�����,并變成為可供后人用靈魂去觸摸的資源存在���;一旦有了觸摸與認(rèn)知��,畫家在其中與先哲心照不宣地相遇乃至神交,由此��,畫家的靈魂也生發(fā)出相應(yīng)的顫動(dòng)��,于是�,遠(yuǎn)逝的歷史由此被喚醒���,并重新活在新世紀(jì)的視野中��。
歸納起來(lái)說(shuō)��,何水法沉思與激情融合的藝術(shù)之路與文本,有這樣三個(gè)特點(diǎn):
一��、有傳承,并從中作出文本解析與價(jià)值重估,且在學(xué)風(fēng)上,堅(jiān)拒浮躁�,唯恐褻瀆千年悠久���、特別是百年以來(lái)的文化精神與審美積淀�����,使之循序漸進(jìn)、借古開(kāi)今。二��、自覺(jué)以當(dāng)代文化語(yǔ)境為背景����,兼融中西藝術(shù)之優(yōu)長(zhǎng)�,在兩者嫁接中,互為借鑒與吸收����,乃至有所發(fā)現(xiàn)�����,自成情懷與格局。三、創(chuàng)新探索�����,百年新中國(guó)畫運(yùn)動(dòng)所凝結(jié)的人文情懷與精神傳統(tǒng)���,在他這里顯露其萌動(dòng)的精神血緣����,文化傳統(tǒng)與精神被他喚醒,并在當(dāng)下創(chuàng)作中呈現(xiàn)為創(chuàng)新的動(dòng)力�����、資源與底蘊(yùn)�����,因而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意義�����。
如果有一種繪畫是為了理想而畫�����,是為了追求而畫�,是面向未來(lái)而畫��;那么�,何水法的作品便是這樣的繪畫����,并在一種身處“萬(wàn)象”中以“直視”的方式去實(shí)現(xiàn)。
作為一種精神見(jiàn)證�,我們把何水法的花鳥(niǎo)畫藝術(shù)看成是一代人和一個(gè)時(shí)代的精神與情感的折射����,把何水法看做我們時(shí)代的花鳥(niǎo)畫的旗手����,是當(dāng)之無(wú)愧的。

凝雪 33×33cm 2013年

晨露新妝 33×33cm 2013年

幽妍 33×33cm 2013年

金盤 33×33cm 2013年